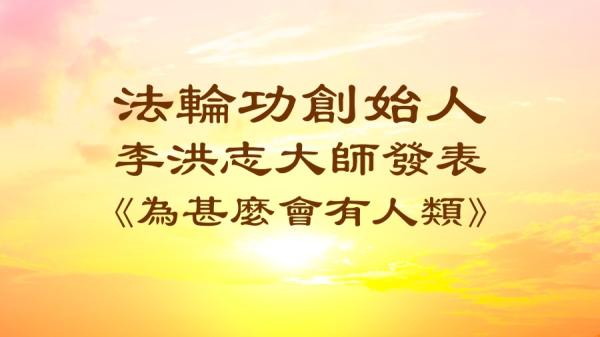故国神游•两宋风华 (45) —— 风起朝堂朋党论 心远江湖岳阳楼
(接上期)
前文提到,庆历四年十一月,宋仁宗下诏禁朋党相讦。这道诏书的背景正是变法派大臣们被反对者们指为“朋党”,而宋仁宗也受到这种论调的影响,开始动摇,从支持变法,转为止步不前。最后,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历新政,就在甚嚣尘上的“朋党论”中戛然而止了。本文就来说说这个“朋党”。
朋党之议由来已久,并不是从庆历新政才开始的。应该说,对于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而言,朋党之议一直是如影随形,阴魂不散。早在景佑三年(公元1036年)五月,时任开封府的范仲淹就已经经历过一次朋党风波了。起因是范仲淹认为宰相吕夷简“进用多出其门”,就是选人、用人,都用自己人,搞小圈子。于是就给宋仁宗呈上一幅《百官图》,图中标记出,怎样是按序升迁,怎样是不按序升迁;怎样是出于公心,怎样是出于私心。后来,两个人又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政见不合,矛盾愈演愈烈,最后吕夷简上宋仁宗那儿告状诉苦,说范仲淹越职言事,离间君臣,引用朋党。范仲淹也不示弱,更加激烈地回怼,于是就被贬知饶州。

庆历变法失败,范仲淹被罢官,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,始终能够泰然处之。(WINNIE WANG/看中国)
当时很多人都为范仲淹发声。集贤校理余靖上疏说:“党其言未合圣虑,在陛下听与不听耳,安可以为罪乎!”意思是如果范仲淹的话说得不合适,您可听、可不听,怎么能因此就怪罪处罚他呢!并请求宋仁宗收回成命。结果余靖因这份上疏被降职。
馆阁校勘尹洙也上疏说:“我与仲淹亦师亦友,也是仲淹一党的,今天仲淹以朋党得罪,我也不应幸免。”结果他也被降职。
馆阁校勘欧阳修则是修书一封,把司谏高若讷痛骂了一顿。司谏是言事官,向皇帝提建议的。欧阳修认为,高若讷在范仲淹因言获罪这件事上,没有劝谏皇帝,是失职,于是在信中痛骂: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!”高若讷被骂急了,就把这封信上呈宋仁宗,于是欧阳修也被贬官。
当时朝中官员们都畏惧宰相吕夷简,不敢去给范仲淹送行。范仲淹离京去饶州那天,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纮、集贤校理王质为他饯行。有人不理解,说范仲淹都被列为朋党了,你还不离他远点?王质说:“范仲淹是贤士,能与他一起被指为朋党,是我的荣幸!”
馆阁校勘蔡襄则奋笔疾书,写了一首大作——《四贤一不肖》诗,赞誉范仲淹、余靖、尹洙、欧阳修,批评高若讷。结果这首诗非常轰动,被时人争相传写,还被拿到书市上去卖,卖书者获利颇丰,大有洛阳纸贵之势。这期间,有契丹使者到来,居然还买了一份带回契丹,张贴于幽州馆。幽州馆是宋朝使臣出使契丹时,被安置居住的场所,有点像现在的国宾馆。这样的诗被张贴在大辽的“国宾馆”里,可见这首诗及这次朋党风波影响之大,不仅轰动朝野,还轰动了友邦。
在范仲淹被贬之后的几年中,因为士大夫们论荐不止,不停地上疏,为他发声,宋仁宗更觉得他们很像朋党,于是在宝元元年十月,再次下诏禁朋党。后来因为宋夏之间发生了战争,范仲淹再度被起用,驻守西北边境,立下大功。接下来就是被召回朝中,主持庆历新政。在这种背景下,朋党之议又死灰复燃了。
前文讲过,庆历三年三、四月间,也就是新政开始之前,宋仁宗将范仲淹、韩琦调回朝中,让他们进入二府,重用为执政大臣,同时又增设谏官。而在景佑三年那场朋党风波中被贬放的官员,像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等人,都被召回,任命为言事官,可以说是大快人心。
国子监直讲石介一高兴,写了一首长诗——《庆历圣德颂》,大赞宋仁宗进贤退奸。贤,当然就是指这些贤能之人,奸呢?指的是一个叫夏竦的人。
夏竦之前也是被委以边事,抵御西夏,但是夏竦畏敌怯战,西夏李元昊曾经张帖榜文说:“得竦首者,予钱三千。”用三千钱悬赏夏竦首级,可见西夏人对他是非常地轻视。在庆历三年三月的人事调整中,夏竦本来是被高升为枢密使,结果在众官的谏阻之下,还没到任就被罢免了。
至于这首《庆历圣德颂》则是传遍朝野上下,轰动程度不亚于蔡襄的那首《四贤一不肖》,连远在眉山8岁的苏轼都看过这首《庆历圣德颂》,可见这首诗影响力之大。但是正是这首长诗,为日后埋下了隐患。
在诗中被指为奸人的夏竦,很不甘心,于是就大造舆论,将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指为朋党。而范仲淹与欧阳修这两个人的性格有点像,都觉得自己公心为国、心怀坦荡,所以不仅不避嫌,不在乎别人怎么议论,甚至还迎风而上。有一次,宋仁宗与大臣们讨论起朋党之事,范仲淹说:“自古以来,邪正在朝,各为一党。”等于是承认他们就是朋党了,不过他们是君子之党。并且说“君子相朋为善”,意思是说这种君子之党是专做好事,对国家是有好处的。
欧阳修更是大笔一挥,写了一篇《朋党论》给宋仁宗。这篇雄文中,欧阳修来了个标新立异,不仅不回避朋党,还赋予了朋党新的含义。他说:“小人无朋,君子才有朋。”为什幺小人无朋呢?因为小人是唯利是图的,有利可图,就结党;无得可图,就互害,所以这个“朋”是伪朋、是假的。君子则不然,所守者道义,以同道为朋,所以同心共济,终始如一,这是真朋。而天子如果能信用君子之真朋,则天下治矣,这个天下就好了。
这篇《朋党论》写得既有道理,又有文采。其实它就是说,不要扣死字眼儿,朋党、不朋党,关键要看人,如果是君子,是一群有道德、有操守的人,多一些更好;如果是小人,结党营私,就会误国、误民。但是现实是,范仲淹、欧阳修的这番自辩,并没能堵住小人之口,也没能挽回新政的命运。庆历四年十一月,宋仁宗再次下诏戒朋党相讦。第二年,庆历五年正月,范仲淹、富弼等变法大臣被罢官,至此,庆历新政正式划上句号。
此时范仲淹已经五十七岁了。走过了大半生的范仲淹,曾经在朝党上谠言论战,曾经在疆场上卫国杀敌,曾经抱着兼济天下之志主持庆历变法,如今他再次因为被指为朋党而离开朝堂,但是对于这一切,他始终能够泰然处之。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之后,为什么能如此云淡风轻,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。
众所周知,人生在世,多少都会有患得患失的时候,可是范仲淹为什么能如此拿得起、放得下?就像他在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中所写: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这真的是一种境界。而他的另一句名言——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不仅成为北宋士大夫们的座右铭,更鼓舞着无数中国历代的读书人,成为他们的精神理想。如果人生是一场修行,这大概就是范仲淹一生修行的所得。
反过来再看他曾经经历过的朋党风波,虽然看起来好像众口嚣嚣,来势汹汹,但当这一切过去之后,会发现这不过是他修行路上的一道风景,不经历狂风暴雨,哪会有云淡风轻?正如本篇标题所云——“风起朝堂朋党论心远江湖岳阳楼”。
(未完待续)